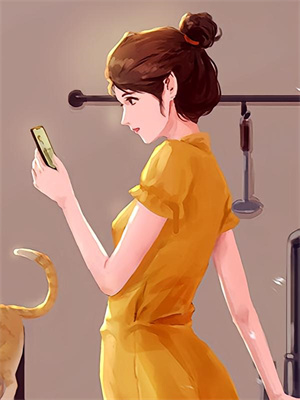简介
精选一篇古风世情小说《路边男的不要捡》送给各位书友,在网上的热度非常高,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有忍冬/沈霜,无错版非常值得期待。小说作者是苍苍草露,这个大大更新速度还不错,路边男的不要捡目前已写138897字,小说状态连载,喜欢古风世情小说的书虫们快入啦~
路边男的不要捡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我喉咙里梗着血块,只剩下急促又空洞的抽气声。眼泪流了,眼睛却死死盯着余音那张青白僵冷的脸,盯着她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淤伤和……某些更不堪的痕迹。
恨。
不是宋老爹被害时那种沉痛冰冷的恨,是一种更尖锐、更疯狂、更带着血腥味的恨!凭什么?凭什么?!宋老爹不明不白死了,现在……连余音,也成了这么一副模样,被扔在这野狗都不屑多闻的乱葬岗!
那帮畜生!他们每一个!都该死!
我猛地爬起来,踉跄着追向那几个家丁离开的方向。他们腰里系着褐色布带,鞋是普通的黑布鞋,但其中一个后脖颈有块铜钱大的胎记,这打扮,不像是顶尖大户,但也绝不是普通贫家。
我像条嗅到血腥味的鬣狗,远远跟着,眼睛瞪得快要裂开,把他们走路的姿势、说话时歪头的习惯,都死死刻进脑子里。他们进了城,拐进一条还算齐整的巷子,进了一座黑漆大门、门口有两个不算威武但也算净石墩的宅子。门匾上写着“吴宅”。
吴粮商。
我记住了。我缩在对街的墙角阴影里,牙齿咬得咯咯响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渗出血来。
报仇!我要报仇!
怎么报?我一个哑巴,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没刀没枪,连这吴宅的门都进不去。
火烧!对!趁夜,翻墙进去,找到柴房或者马棚,一把火烧了这吃人的魔窟!烧死那些畜生!烧死他们!
或者……卖身进去?对,卖身!假装流民,卖身进吴家做最低等的粗使丫头。然后……然后想办法,在井里下毒?在饭菜里动手脚?或者趁夜,摸到那吴粮商的房里,用剪子,用簪子,用石头……捅死他!还有那些帮凶!
我脑子里翻腾着无数血腥又混乱的念头,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。
宋老爹我护不住,余音我也护不住,我活得像个笑话!大不了,和这帮畜生一起死!黄泉路上,我拉着他们,去给余音磕头赔罪!
接下来的几天,我像游魂一样在吴宅附近转悠。我观察他们倒垃圾的时间,看侧门哪些婆子常出入,记下院墙哪处有棵歪脖子树可以借力。我去野地里找可能有毒的植物茎,磨尖了捡来的碎瓷片。我试着在破庙的泥地上,用树枝练习怎么猛地刺出、怎么勒紧脖子。
我计划着,盘算着,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。
就在我觉着准备得差不多了,打算第二天就去人市上卖身进吴家的前夜,吴宅那条街喧哗起来。
火把的光亮撕破黑暗,沉重整齐的脚步声,金属甲片的碰撞声,粗暴的呵斥和哭喊声……和余音家被抄时,一模一样!
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,我竖着耳朵去听,“这狗东西,囤粮抬价!”
“去年大雪,多少人家断了炊,他倒好,把粮仓锁得死紧,等着米价翻着番地涨!”
“不止呢,听说他还通敌,把粮食偷偷运出城去,卖给城外的反贼!”
通敌,囤粮,两条罪名,条条都是死罪。
火光晃动间,我看到一个穿着绸缎、肚腩凸起的中年男人被两名军汉从正堂里拖出来,他满脸油汗,嘴里似乎还在嚎叫求饶,下一刻,雪亮的刀光一闪——那颗肥硕的脑袋就跟身子分了家,滚到台阶下,眼睛还惊恐地瞪着。血,喷得老高。
是那吴粮商!没错!就是他!
我死死盯着那颗头颅,盯着那具瘫软的无头尸体,心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,一种从骨髓里窜上来的、滚烫又冰凉的战栗!痛快!看!!现世报!不用我动手,老天爷替我收了这畜生!
火光继续晃动,更多人影被驱赶、被砍。有男有女,有穿绫罗的,也有穿粗布的。那个后脖颈有胎记的家丁,我看见他抱头想往后院钻,被一个骑兵追上,马刀从后背捅入,前穿出!他扑倒在地,抽搐两下,不动了。
好!又一个!
我笑了。先是低低的、压抑的笑,到后来,变成了肆无忌惮的、几乎要岔气的笑。
我拍着手,看着那些曾经锦衣玉食的人,一个个倒在血泊里。看着那朱漆大门上的鎏金匾额,被官差用刀劈成两半,看着那亭台楼阁,被点起一把大火,烧得噼啪作响。
那种快意,像是毒藤一样,从我的心底里钻出来,缠满了我的四肢百骸。我浑身发烫,血液在血管里疯狂地奔涌,仿佛下一刻就要冲破皮肤。
可笑着笑着,我的声音突然哑了。
火把依旧通明,兵丁们开始进进出出搬运尸体,扔上板车。
痛快吗?
痛快。
可那又怎样呢?
他的死,是因为触怒了朝廷,不是因为我,不是因为余音,不是因为那些被他得家破人亡的百姓。
快意像水一样涌上来,又像退一样迅速褪去,剩下的,是一片空茫。
我就这么……看着?仇,就这么报了?
余音呢?她受的那些屈辱折磨,她临死前的冰冷……就值这几颗陌生兵丁砍下的、肮脏的头颅?
不。不够。远远不够。
可……还能怎样?
凶手死了,帮凶也死了,房子空了。
这世道,人都不用你亲自动手。它自己就吞吃一切,连仇恨都吞得净净,只留下一个被掏空了魂儿的躯壳,站在原地,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
下一个被抄家的,会是谁?
下一个像我一样,在火场外茫然站立的,又会是谁?
我极其缓慢地从臭水沟边爬起来。腿麻了,身子晃了晃。最后看了一眼那血迹斑斑的吴宅大门,和远处被拖走的尸首板车。
然后,转过身,一步,一步,朝着背离那片血腥的方向走去。手里一直紧攥着的用来报仇的碎瓷片,不知何时已经掉了。
也好。
风吹过来,带着未散尽的血腥和焦糊味。我舔了舔裂的嘴唇,尝到一点铁锈般的咸味,不知是别人的血溅到了风里,还是我自己又把嘴唇咬破了。
走吧。
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。
像仅存的本能,找个地方,把这具还没彻底烂掉的皮囊,塞进去。至于里面是空的,是冷的,还是塞满了化不开的冰碴子,没人在乎,我自己……好像也不太在乎了。
走吧。走吧。
嘴里念着,脚下挪着,饿了,就趴在地上跟野狗抢点不知什么东西的残渣;渴了,就喝沟里发绿的水;困了,随便找个能避风的土坎一蜷。
脸上宋老爹给弄的那道假疤还在,混着新添的污垢,更像个真正没人要的丑怪。头发打结,衣衫褴褛,连流民堆里最邋遢的婆子,看见我都嫌晦气,绕道走。
走到哪里,不知道。
活下去?为什么活?不知道。
报仇?仇人在哪儿?不知道。
好像什么都知道了,又好像什么都与我无关了。我只是这乱世荒原上一缕飘荡的、麻木的影子。
那天傍晚,又冷又饿,眼前一阵阵发黑。我瘫在一座不知名破桥的桥洞下,看着浑浊的河水慢吞吞地流。
忽然觉得,就这样顺着水漂下去,或者一头栽进去,也挺好。省得再走,省得再饿,省得再想起余音那双空洞的眼,想起宋老爹冰冷的尸身。
我闭上眼,身子往冰冷的河水方向歪了歪。
“喂!”
一个有点沙哑、却带着劲儿的女声像块石头砸过来。
我迷迷糊糊睁开眼。
一个年纪比我大几岁的女子蹲在我面前,同样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麻布短褐,脸上有灰,头发用草绳胡乱绑着,可那双眼睛,亮得惊人,像暗夜里突然擦亮的火石。她手里捏着半块黑乎乎的、掺着麸皮的饼子,掰了更小的一块,直直递到我嘴边。
我愣住了,没动。
“吃点吧,”她的声音有些沙哑,却很脆,“我看你还有口气,眼神还没死透,嘛跟自己过不去?饿死了,可就真啥都没了。”
我看着她,喉咙得发不出任何声音,只是摇头。
她啧了一声,不由分说,把那小块饼子塞进我手里。“捏紧了!我叫小禾,禾苗的禾。你叫啥?”
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半块救命的饼子,指尖微微颤抖。良久,我用手指,在地上划了两个字:忍冬。
“……嗯,这个字念……忍?冬?”她凑过来看。
我点点头,她眼睛一亮,“好啊!我就喜欢忍冬花!又皮实,冬天也冻不死,开起来还好看!你这名字好!”
她的话很简单,却像一块小小的火石,在我心底擦出了一点微弱的火星。我慢慢把饼子放进嘴里,用力咀嚼,这是逃亡以来,尝到的第一口有滋味的东西。
小禾很自然地挨着我坐下,“我看你一个人,也没个伴儿。我要北上,去冀州那边寻亲。我有个远房表兄,在清河崔氏府里做事,听说伺候的是一位公子。那可是了不得的人家!你……要不要跟我一道?路上有个照应,总比一个人等死强。”
我抬头看她,眼里是死水般的茫然。
她拍了拍我的肩膀,力道不小,拍得我身子一歪。“咱们先去找个大户人家的庄园或者坞堡,卖力气活,攒点路费,也打听打听门路。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”
见我不说话,她默了一会儿,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盯着我,声音压低了些,却更沉:“你虽然不吭声,但我瞧得出来,你心里憋着一股气,一股子狠气,是恨吧?恨那些糟践了你、害了你亲人的人?”
我猛地一颤,手指下意识收紧,指甲掐进掌心。
她顿了顿,“我爹妈死得早,嫁了个男人,没两年家乡闹兵灾,男人没了,婆家嫌我克夫,把我扫地出门……啥腌臜气没受过?啥白眼没看过?不也还喘着气,没让阎王收走么?”
她语气平淡,像在说别人的事,可眼睛里瞬间掠过的痛楚,我却看得分明。
我心里一紧,抬眼看她。
她一把抓住我冰凉的手,她的手心粗糙,布满茧子和细小的伤口,却滚烫。“所以!妹子,恨,就记着!但光恨顶屁用?你得先活着!活得比那些王八蛋长,活得比他们硬朗,才有机会把这口恶气吐他们脸上!听姐的,咱先想法子把命保住,把身子骨养结实点,再说别的!”
活着。先活着。
这两个字,从小禾嘴里说出来,不是沈医娘那种沉甸甸的嘱托,不是柳婶儿那种含泪的哀求,不是余音那种空洞的诀别,她的眼里只有一种近乎蛮横的、对“活下去”这件事本身的执着。
我反手,用尽此刻能凝聚的全部力气,紧紧抓住了她滚烫的手,用力点了点头。
小禾就像一道横冲直撞的光,硬生生劈进了我一片死寂的世界。她带着我,混进一股更大的、往北迁徙的流民队伍。
路上,她教我辨认更多能吃的野菜野果,哪怕是最苦最涩的,她也能说出哪部分毒性小些。
“喏,这个马齿苋,掐嫩头,用水焯一下,虽然还是难吃,但吃不死人。”
“那个灰灰菜的,埋火堆里煨熟了,勉强能顶饿。”
夜里寒风刺骨,我们就挤在破庙墙角、草堆里,紧紧挨着,互相取暖。她话多,会讲她家乡河沟里摸鱼的事,讲她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人,也会低声咒骂世道,骂那些刮地皮的贪官,骂那些千刀的乱兵。
跟着流民大,不知走了多久,终于看到远处地平线上矗立起一道灰黄色的高墙,墙头有箭楼,那就是坞堡,本地豪强聚集宗族、部曲自保的土围子。堡外依附的流民窝棚密密麻麻,像一片巨大的的烂疮。
小禾拉着我,挤过臭气熏天的窝棚区,直奔坞堡侧门。那里有几个管事模样的人,正挑拣着流民里还算看得过眼的青壮。
“两位爷!行行好!收下我们吧!我们能活!什么都能!”
小禾挤到最前面,声音又亮又脆,脸上堆着笑,却把腰板挺得直直的,“我力气大,能舂米,能挑水,能喂牲口!我这妹子,”她一把将我拽到身前,“手巧,听话,能缝补,能打扫,吃得还少!”
那管事斜睨着我们,又捏了捏小禾结实的胳膊,从鼻子里哼了一声:“进去吧。西边最破那排窝棚,找刘婆子领活儿。丑话说前头,偷懒耍滑,立马滚蛋!死了残了,自己找地方埋,堡里不管!”
我们总算有了个能挡雨的窝棚,每天天不亮就起,阿禾被分去舂米。那石臼又大又沉,木杵抡起来,砸下去,发出沉闷的咚咚声,从早响到晚。她很快成了那一组最能的,别人一天舂三斗米累得胳膊都抬不起,她能舂四斗半,汗水把粗麻短褐浸透,贴在身上,勾勒出结实有力的线条。监工的婆子都对她另眼相看,有时会多给她半勺稠粥。
我被分去浆洗和缝补。成堆的、散发着汗臭的衣物,在冰冷的河水里泡,用木棒捶打,手很快就冻得通红,又肿又痒。晚上,就着豆大一点的油灯缝补那些磨破的衣裳,针脚必须细密,否则要挨骂。
吃的是粗糙的麦粒混着麸皮,有时还掺着没筛净的沙土和稗子,硬得硌牙,得就着稀薄的、只有几片烂菜叶的豆叶汤才能咽下去。
阿禾因为能,有时能多得半勺饭或一小撮盐。她总是偷偷分我。
“吃!看你瘦得跟麻杆似的,风一吹就倒!多吃点,长点力气!”她不由分说,把稠的拨到我碗里。
我额前的刘海始终厚重,那道假疤成了我的符,让我在这混乱的地方少了很多麻烦。
但麻烦还是来了。
那天河边,头毒,水汽蒸得人发晕。我蹲在大石后的浅滩,捶打一堆脏衣。汗顺着额角往下淌,痒得难受。我撩起河水,胡乱抹了把脸,想凉快些。
水有点急,冲开了我额前黏湿的厚重刘海,也把脸颊边缘的污泥和那假疤的边角冲得有些翘起。
我正低头,想用手把翘起的疤按回去,一个阴影猛地罩下来,带着浓重的汗馊和酒气。
是管仓库杂物的胡癞子。他眯着那双浑浊发黄的眼,直勾勾盯着我刚刚擦洗过,露出些许本色的脸颊和脖颈。
“嘿……老子就说,这小哑巴洗净了,指定不赖……”
他咧嘴笑,露出一口黄黑烂牙,“这疤……是假的?让爷瞧瞧真的模样……”
他说着,一只油腻粗黑的手就伸过来,不是摸下巴,是直接朝着我脸颊、那道翘起的假疤抓来,想把它撕掉!
我吓得魂飞魄散,猛地向后一仰,想躲开。可蹲久了腿麻,动作慢了半拍,被他另一只手铁钳似的攥住了手腕。
他眼神黏腻地在我脸上,嘿嘿笑着,一只手就往我衣襟里探,嘴里不不净:“哑巴好,不会叫,省事……”
他力气极大,拽着我往芦苇荡里拖,嘴里喷着酒气,一把将我按在地上,油腻的嘴唇凑了过来,我拼了命地挣扎,喉咙里发出的“啊啊”声,另一只手胡乱抓挠,指甲划破了他手背,他却像感觉不到疼,反而更兴奋,嘴里不不净地骂着,就要来扯我本就破烂的衣裳。
绝望瞬间淹到头顶。我太瘦弱了,十四五岁的年纪,长期饥饿,力气得像鸡崽。挣不开,踢不动,那些关于余音、关于乱葬岗尸体的记忆碎片猛地涌上来,恶心得我浑身发抖。
就在那脏手快要碰到我衣襟的刹那——
“胡癞子!我你八辈祖宗!”
一声炸雷似的怒骂,伴随着一阵急促沉重的脚步声,小禾像头被激怒的母豹子冲了过来,她手里赫然攥着一块碗口大的、边缘锋利的石头,那胡癞子一惊,刚回头,小禾手里的石头就狠狠砸在了他肩膀上。
“嗷——!”胡癞子惨叫一声,松开了我,踉跄着后退。
小禾不依不饶,扑上去,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、脸上,一边打一边骂:“瞎了你的狗眼!敢动我妹子!老娘今天撕了你!”
“欺负哑巴不会喊是吧?老娘替她喊!让全堡的人都来看看你这畜生样!”
她打得又凶又泼,那胡癞子起初还想还手,被小禾一石头砸在膝弯,又挨了几记狠的,终于怕了,连滚爬爬地跑了,边跑边骂:“臭娘们!你们给我等着!”
小禾喘着粗气,扔了石头,转身一把抱住还在发抖的我。“没事了,忍冬,没事了!姐在这儿!”她拍着我的背,声音还带着怒意,手却有点抖,“那王八蛋!下回再敢来,姐剁了他的爪子!”
我紧紧抓着她的衣服,把脸埋在她散发着汗味和麦糠味的怀里,无声地大哭起来。
从那以后,小禾几乎成了我的影子。她去舂米,得空就绕到浆洗处看我一眼;我晚上缝补,她就在旁边帮我理线,嘴里叨叨着今天听来的闲话。有她在,堡里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,收敛了很多。
小禾人缘也好。她力气大,肯帮忙,谁家窝棚漏了,她帮着糊把泥;谁被监工刁难,她敢上去说两句公道话。很快,西边窝棚这片,大家都叫她“禾姐”。
她就是我在这个冰冷坞堡里,唯一的光。她让我知道,就算活得跟野草一样贱,也得挺直了,有刺,能扎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