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非常热门的一本历史古代小说,布袋行,已经吸引了大量书迷的关注。小说的主角契此陈三宝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魅力,让读者们深深着迷。作者户外老美以其细腻的笔触,将故事描绘得生动有趣,让人欲罢不能。主要讲述了:汴梁城外的乱并未掀起太澜。禁军驱散了人群,抓了几个趁乱偷窃的泼皮,将“妖僧作法”的流言斥为无稽之谈,定性为“刁民借机生事”。在朱温治下,这类“不祥”消息向来被严密管控,很快便沉入这座都城深不见底的淤泥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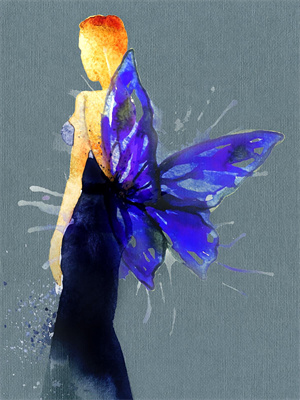
《布袋行》精彩章节试读
汴梁城外的乱并未掀起太澜。禁军驱散了人群,抓了几个趁乱偷窃的泼皮,将“妖僧作法”的流言斥为无稽之谈,定性为“刁民借机生事”。在朱温治下,这类“不祥”消息向来被严密管控,很快便沉入这座都城深不见底的淤泥里。
契此向北又走了数,刻意避开大路,专拣荒僻小径。淮北平原的冬末春初,是最难熬的时节。积雪消融未尽,冻土开化,道路泥泞不堪,寒风依旧凛冽,裹挟着沙土,刮得人脸颊生疼。田野空旷,偶尔可见废弃的村落,断壁残垣间,只有野狗和乌鸦盘桓。
这一午后,他正沿着一条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古道前行,远处忽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,并非一两匹,而是训练有素的一队。契此迅速闪身,隐入道旁一片枯败的芦苇丛中。
蹄声由远及近,约莫十数骑,皆黑衣窄袖,腰佩障刀,背负短弩,马匹雄健,行动间无声而迅捷,只有马蹄踏过泥泞的闷响。他们并未狂奔,而是以一种精确搜索的姿态,控马缓行,目光锐利地扫视着道路两侧。为首一人,面白无须,眼神阴鸷,即使在马背上,背脊也挺得笔直,透着宫中内侍特有的矜持与阴冷。
契此屏息。这些人身上有淡淡的、与这片旷野格格不入的熏香气味,那是宫廷和贵族才用得起的名贵香料。是梁宫的密探,或者更直接,是皇帝私人的“察事厅”人马。
队伍在离契此藏身处不远的地方停下。为首内侍抬手,队伍静立。他眯眼望着前方岔路,声音尖细平稳:“分三路,前五继续追那晋谍。剩下人,随我去会会那位……‘收灯’的法师。”
“陈公公,”一名手下低声道,“那和尚行踪诡秘,城外那晚之后便失了踪迹,传言多不可信,未必真有其人,或是愚民以讹传讹……”
“宁信其有。”陈公公打断他,嘴角扯出一丝没有温度的弧度,“陛下近心绪不宁,夜梦多魇,太医署那帮废物束手无策。若真是有些道行的异人……或许能为陛下分忧。再者,”他眼神骤然转冷,“若只是个招摇撞骗、扰乱民心的妖僧,正好拿了,以正视听。找!沿着这方圆五十里,细细地筛!”
“是!”
队伍再次分开,两人随陈公公拨马转向另一条小路,其余人散入荒野。
契此在芦苇丛中静静伏着,直到蹄声彻底远去,旷野重归寂静。他抖落身上的枯草碎叶,望着陈公公消失的方向,若有所思。宫中的触角,到底还是伸过来了。不是因为那晚“收灯”的把戏多高明,而是那位坐在龙椅上、猜忌刻薄的皇帝,正被不安和疑心病煎熬,任何一点“非常”的苗头,都会被纳入他恐惧与掌控的罗网。
是福是祸?他摸了摸肩上的布袋。布袋沉静无言。
他并未改变方向,依旧向着北方,但步伐更缓,更留意周遭动静。傍晚时分,他在一处背风的土崖下找到个浅浅的凹洞,勉强容身。生了一小堆火,烤着仅剩的一块硬饼。火光跳跃,映着土崖粗糙的纹理。
夜半,他忽然惊醒。不是声音,是一种被注视的感觉。他悄然睁眼,火堆已熄,只有余烬微光。洞口外,月光清冷,三个黑影如鬼魅般立在那里,无声无息,正是白那陈公公和他的两名手下。他们竟去而复返,精准地找到了这里。
“法师好警觉。”陈公公的声音在寒夜里格外清晰,带着一丝赞许,更多的却是审视,“贫僧契此,不敢称法师。”契此坐起身,并未慌乱。
“能于上元夜,不动声色收走半条街市灯火,令愚民惊惶,流言四起,这手段,称一声‘法师’也不为过。”陈公公踱进凹洞,目光如锥,上下打量着契此和他身旁的布袋,“咱家奉旨办差,请法师移步,与咱家走一趟。”
“去何处?”
“自然是该去的地方。”陈公公不置可否,“法师是明白人。陛下闻法师之名,颇有兴趣。此乃机缘,莫要自误。”
话说得客气,但洞外两名手下手已按上刀柄,气息锁定了契此所有可能逃脱的方位。这是不容拒绝的“邀请”。
契此沉默片刻,终是点点头:“既是陛下相召,贫僧不敢推辞。只是贫僧这身污秽,恐污了贵地。”
“无妨。”陈公公侧身,“请吧。”
没有绳索镣铐,但契此知道,自己已在这三人的严密监视之下。他背起布袋,走出凹洞。洞外拴着三匹健马,还有一匹空着的。陈公公示意他上马。
马蹄嘚嘚,在月色下向北疾行,却不是回汴梁城的方向,而是折向东北。约莫一个时辰后,前方出现一座倚山而建、守卫森严的庄园,黑沉沉一片,只有零星几点灯火,宛如蛰伏的兽。这不是皇宫,更像是离宫或某处秘密别苑。
从侧门进入,穿过几重门禁,最终来到一处偏僻安静的院落。院中只有正房亮着灯,门窗紧闭,听不见里面丝毫声息。陈公公让两名手下守在院门,自己领着契此走到房前,躬身低语:“陛下,人带来了。”
里面沉默片刻,一个略显沙哑、疲惫,却带着不容置疑威严的声音响起:“带进来。”
房门推开。屋内陈设简单到近乎朴素,与皇帝身份极不相称。只一榻、一案、一灯。榻上坐着一人,披着玄色常服,未戴冠冕,头发略显花白散乱,正是后梁开国皇帝,也是以暴虐猜忌著称的朱温。他面色晦暗,眼窝深陷,目光却依旧锐利如鹰,此刻正带着审视、疲惫与一丝掩饰不住的烦躁,盯着走进来的契此。
朱温比契此想象中更显老态和……不安。这位弑君篡位、在战场上人如麻的枭雄,此刻更像一头被困在笼中、伤痕累累、却更加危险的病虎。
陈公公无声退到角落阴影里,仿佛不存在。
“你就是那个,收走民间灯火的和尚?”朱温开口,声音不大,却压得屋内空气一沉。
“贫僧途经汴梁,见灯火有异,略施小术,惊扰民间,实属不该。”契此合十,语气平静。
“小术?”朱温扯了扯嘴角,“能令灯火齐黯,民心浮动,这可不是小术。说说,你是怎么做到的?”
“光影之道,聚散之理。”契此答得含糊,“心有所感,外显于物。”
朱温盯着他,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破绽,半晌,忽然换了话题:“朕近,睡得不好。总梦到一些……旧人旧事。宫中术士,太医,皆言是心神劳损。你既有异术,可能为朕解之?”
这不是求医,是试探,也是命令。
契此垂目:“贫僧不解梦,只解眼前物。”
“哦?”朱温身体微微前倾,“那你看看朕这眼前,有何物需解?”
契此抬起眼,目光平静地迎上朱温审视的视线,又缓缓扫过这间空旷冷寂的屋子,最后落回自己肩头的布袋上。他忽然解下布袋,放在地上,解开系绳。
在朱温和阴影中陈公公警惕的注视下,他将手探入袋中,摸索片刻,抓出一把东西,摊开在掌心。
不是符咒,不是丹药,而是一把混杂的豆子和沙子。黄豆与沙粒大小相近,颜色却分明。
契此将这把豆与沙的混合物,轻轻放在朱温面前的案几上。
“陛下请看,”他声音平和,“此乃贫僧途中所得。陛下若能分清,哪些是豆,哪些是沙,或许……便能看清眼前之物,乃至梦中之事。”
朱温眉头紧锁,看着那堆混杂之物。这算什么问题?豆是豆,沙是沙,一目……他凝神细看,却因灯火昏暗,豆与沙颜色质地相近,混杂一处,竟一时难以迅速精确分离。他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无名火,这和尚是在消遣朕?
他刚欲发作,契此却已俯身,用袖子在案几上轻轻一拂。
哗啦一声,那堆豆与沙被他拂落地面,大部分滚进了案几与地面之间的石板缝隙里,消失不见。
“你!”朱温怒意上涌。
契此直起身,对朱温的怒色恍若未见,只是指着那些缝隙,淡然道:
“分不清,便不必强分。且让它们留在那里。”
“待来年春雨浸润,阳气萌动。”
“是豆的,自会发芽。”
“是沙的,依旧沉默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澄澈地看着朱温:
“到时候,天地自会分明。”
“陛下又何必,于此刻昏暗灯火下,苦苦分辨,徒增烦扰?”
话音落下,屋内死寂。
朱温脸上的怒意僵住,慢慢转为一种更深的、混杂着惊疑、恍然与疲惫的复杂神色。他死死盯着地上那些缝隙,仿佛真能看到里面埋藏的豆与沙。这疯和尚的话,似答非答,似解非解,却像一冰冷的针,刺破了他近萦绕不去的某些梦魇与焦虑——那些混乱的往事,那些难以分辨的忠奸,那些无法掌控的未来……不正如这豆与沙,纠缠难解?
苦苦分辨,徒增烦扰……天地自会分明……
良久,朱温长长吐出一口浊气,靠回榻上,闭上眼,挥了挥手,声音透出浓重的倦意:“罢了……陈伴伴,带他出去。安排个僻静处住下,明……再议。”
陈公公无声上前,示意契此离开。
契其捡起布袋,重新背上,对闭目不语的朱温合十一礼,转身退出。
房门在身后关上,隔绝了屋内那令人窒息的压抑与一个帝王深藏的恐惧。
陈公公引着他来到院落另一侧一间狭小的厢房,留下一句“莫要随意走动”,便锁上门离去。
契此在冰冷的炕沿坐下。窗外月色凄清。他知道,自己暂时安全了,但也更深地卷入了危险的旋涡。朱温没有立刻他,甚至可能真对他那番“豆沙之论”产生了某种扭曲的寄托。但这君恩,比刀剑更无常。
他摸了摸布袋。今夜,它装下了一捧豆与沙,也装下了一个帝王瞬间的恍惚与更深的不安。
远处,似乎传来夜鸟凄厉的啼叫,划破离宫沉重的寂静。
(第二卷 第七章 终)
小说《布袋行》试读结束!